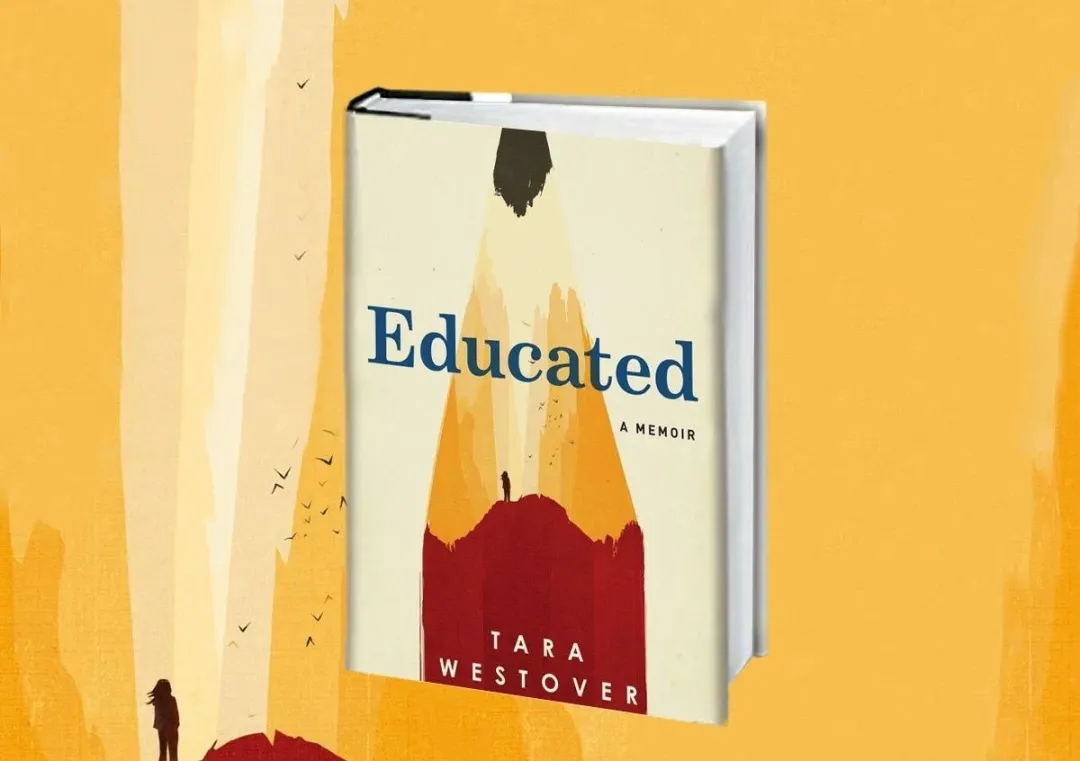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经历和历史。****接受教育,但不要让你的教育僵化成傲慢。教育应该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它不应该使你的偏见变得更顽固。如果人们受过教育,他们应该变得不那么确定,而不是更确定。他们应该多听,少说,对差异满怀激情,热爱那些不同于他们的想法。**
——塔拉•韦斯特弗,《福布斯杂志》访谈
韦斯特沃家的七个兄弟姐妹中,塔拉和另外两人离开了父母,而且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哪怕在一个“正常”家庭里,三个孩子都取得博士学位的情况也让人刮目相看。三人一定经历了不同寻常的童年,使他们养成了某种坚韧的品格,让他们学会了持之以恒。塔拉的父亲教育孩子们说,他们什么都可以自学,而塔拉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
塔拉在学校里学习了哲学和历史后,才开始相信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我觉得这很有趣。由于她从未上过学,她的世界观完全是由父亲塑造的。父亲相信阴谋论,所以她也相信。直到进入了杨百翰大学,她才发现被父亲当做是事实的观点还能从其它视角解读。比如在艺术史教授提及纳粹大屠杀前,她对此一无所知。她不得不去做了一番调查,才形成了有别于父亲的观念。
人们只看到我的与众不同:一个十七岁前从未踏入教室的大山女孩,却戴上一顶学历的高帽,熠熠生辉。
只有我知道自己的真面目:我来自一个极少有人能想象的家庭。我的童年由垃圾场的废铜烂铁铸成,那里没有读书声,只有起重机的轰鸣。不上学,不就医,是父亲要我们坚持的忠诚与真理。父亲不允许我们拥有自己的声音,我们的意志是他眼中的恶魔。
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历史博士……我知道,像我这样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无知女孩,能取得如今的成就,应当感激涕零才对。但我丝毫提不起热情。
我曾怯懦、崩溃、自我怀疑,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恶臭熏天。
直到我逃离大山,打开另一个世界。
那是教育给我的新世界,那是我生命的无限可能。
“我担心教育正变成一根棍子,有些人利用它来打击别人,使其屈服;我也担心教育正在变成让人自大的东西。”她说,“我觉得接受教育其实只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它能培养自我意识,让你认识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它是一种了不起的机制,可以让人连接彼此,促进平等。”

书摘:
这是门关于莎士比亚的课,我选它是因为我听说过莎士比亚,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但现在我才意识到我对他一无所知。那只是我听过的一个名字,仅此而已。
一阵狂风扫过护栏,克里博士摇晃起来,抓住墙壁不放。我走上屋脊,好让他靠在扶壁上。他盯着我,等着我解释。
“我给干草棚盖过屋顶。”最后我说。“这么说你的腿更有力?就是因为这个你才能稳稳地站在风里吗?”
回答之前,我思考了片刻。“我能在风中站稳,是因为我不是努力尝试站在风中,”我说,“风就是风。****人能受得了地面上的阵阵狂风,所以也能禁得住高空的风。它们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头脑中怎么想。”他茫然地看着我,不明白我的话。
“我只是站着,”我说,“你们却都降低身体,试图弥补,因为高处让你们害怕。但蹲着走和侧身走并不自然,这样反而让自己变得脆弱。如果能控制住恐慌,这风就不值一提了。****”
“这对你来说没什么。”他说。
意识到个人对过去的了解是有限的,并将永远局限于别人所告诉他们的。我知道误解被纠正是什么感觉——改变重大的误解便是改变了世界。现在,我需要了解那些伟大的历史看门人是如何向自己的无知和偏见妥协的。****我想如果我能接受他们所写的东西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带有偏见的话语和修正过程的结果,也许我就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认同的历史不是我被教导的历史。爸爸可能是错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卡莱尔、麦考利和特里维廉也可能是错的,但从他们争论的灰烬中,我可以构建一个世界,生活在其中。当我知道了地面根本不是地面,我希望自己能站在上面。
我在杨百翰大学的教授们没有一个像斯坦伯格教授那样检查过我的写作。没有逗号、句号、形容词或副词都会引起他的兴趣。语法和内容、形式和实质对他而言同等重要。在他看来,一个写得不好的句子是想法构思欠佳,但语法逻辑同样需要修改。“告诉我,”他会说,“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用逗号?****你希望在这些短语之间建立什么关系?”当我给出解释,他有时会说“完全正确”,有时会对句法进行冗长的解释来纠正我。
“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的内心。”他说,“斯坦伯格教授说这是《卖花女》。想想那个故事吧,塔拉。”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如炬,声音洪亮,“她只是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伦敦人。直到她相信自己。那时,她穿什么衣服已经无关紧要了。”
我原以为他们会在路边丢下我,但爸爸坚持要陪我穿过机场。他们等着我托运行李,跟着我走到安检口。似乎爸爸想等到我在最后一秒改变主意。我们默默走着。到达安检处,我跟他俩拥抱道别。我脱下鞋子,拿出笔记本电脑和相机,穿过检查站,重新装好物品,准备登机。就在这时,我回头一瞥,看见爸爸还站在安检口目送我离开。他的双手插在口袋里,肩膀耷拉着,嘴巴松弛。我挥挥手,他向前走了几步,好像要跟上来。我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一刻:当高压电线将旅行车盖住,母亲被困在车内时,爸爸站在旁边,一副无助的样子。我拐过弯,他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势。父亲的那个形象我将永远铭记:他脸上的表情充满爱意、恐惧和失落。我知道他为什么害怕。我在巴克峰的最后一夜,就是他说不会来参加我毕业典礼的那一夜,他无意中吐露过。“如果你在美国,”他低声说,“无论你在哪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去找你。****我在地下埋了一千加仑汽油。世界末日来临时我可以去接你,带你回家,让你平平安安的。但要是你去了大洋彼岸……”
(这部分读着有种朱自清笔下《背影》的感觉) 虽然是那样的一位父亲
过去是一个幽灵,虚无缥缈,没什么影响力。****只有未来才有分量。
戏剧上演时,不知为何,我无法再穿过镜子,将十六岁的自己释放出来代替我。
在那一刻之前,她一直在那里。无论我看上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我的教育如何辉煌,我的外表如何改变——我仍然是她。我充其量不过是内心分裂的两个人。她在里面,每当我跨进父亲家的门槛,她就出现。 那天晚上我召唤她,她没有回应。
她离我而去,封存在了镜子里。在那一刻之后,我做出的决定都不再是她会做的决定。它们是由一个改头换面的人,一个全新的自我做出的选择。
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 而我称之为:教育。
与其说教育改变人生我更倾向于是教育改变了我们于这个世界沟通交流的方式。同时我也很高兴,塔拉有泰勒这样一个哥哥,理查德这样的朋友,还遇到了乔纳森·斯坦伯格教授等等,当然也是离不开作者本人的好奇心与努力的。